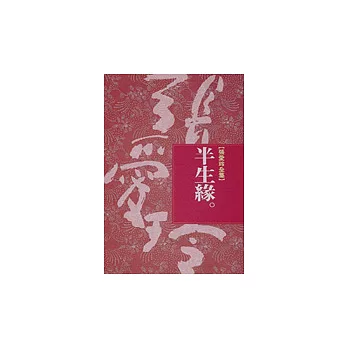
*高手活動文傳送門:點這裡
*嘛對不起我又拖稿了
*11000+,三分糖七分虐,BE預警
*題材取自電視劇《情深緣淺》,原著為張愛玲著半生緣
*免責聲明:因劇情需要某些設定可能違反現實人物背景,全文角色皆為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以下正文***
「阿南,那個小矮子又來了。」說話的女人天生一副媚骨,一頭深棕色大波浪捲髮一看就知道出自上海最有名的髮廊,只有上流舞女才有資格去做頭髮。
「別再說她矮子了,免得人家又生氣。」被稱呼「阿南」的年輕女子闔起手上的書——曹雪芹的《紅樓夢》——乾燥花製成的書籤夾在「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她往窗戶外一望,矮個子女孩捧著一束香水百合,立在玄關外,看到樓上冒出頭的兩人,她揮揮手,笑開來,嘴裡的虎牙、頰邊的梨渦都襯著那圓潤的五官,越發可愛。
「今天是七夕吧,姊?」被稱為阿南的女子問道。
「是,妳們小倆口的好日子,還要我提醒。」長著媚骨的女人心不甘情不願地答道。
「確實,我欠她一次。」阿南淡漠的臉上有了漣漪,「金家小姐沒有約妳出去嗎?」
「加班,臭外科醫生。」女人叉起雙手「哼」了一聲,「害我這大好日子還得上班,誰像妳家那個富二代整天遊手好閒。」
「姊姊別氣了嘛,給妳帶好東西回來好不好?」阿南見對方很是不悅,連忙出主意安撫。
「妳愛帶就帶,不帶就嫁去孫家好了。」女人憋不住,笑出聲來,「趕緊換件衣服滾吧,別讓人家等了。」
阿南笑打了姊姊兩下,邁著輕快的步子換衣服去。
***
湊崎紗夏是湊崎家獨女,父親曾是名震上海的大商人,可惜前些年突然猝逝,幸得留下巨額遺產供母女倆相依為命度過後半生。
其後不久,湊崎家的姻親——名井家的男人們相繼在戰亂中過世,名井南的母親拋下孤女人間蒸發,湊崎母看著人家可憐,便把名井南接來家裡一起生活。
名井南雖然年僅二十出頭,卻已從日本學成歸國,目前在上海日報當自由作家。
而出現在湊崎家樓下的矮個子名叫孫彩瑛,年方十九,是上海巨賈孫承煥的么女,據說小小年紀便展現不凡的經商天賦,現在就幫著父親管孫宅隔壁一間小商行的帳。
要說兩個涉世未深的年輕女人怎麼認識的,套湊崎紗夏的話說,就是玄,她只知道孫彩瑛某天不小心看到上海日報上名井南投稿的小說,回過神來兩人就在一起了。
自此,名井南逢年過節除了跟湊崎母女好好吃頓飯,就是讓孫彩瑛那個小老虎黏著去逛街。
你問湊崎紗夏小老虎是誰,她一定會吐著菸圈,翹著一雙大長腿,好整以暇地說,「毛茸茸的短髮,圓滾滾的大眼睛,倆虎牙,不是老虎是什麼?」
***
即便是傍晚,街市最熱鬧的時候,名井南依然穿得低調,灰色繡花旗袍、黑呢絨披肩,頭上戴個靛色綴水鑽髮箍,稍不留神就會隱身在滿大街的西裝革履中。
「阿南,妳適合更鮮豔的顏色。」兩人在一間鐘錶店停留時,孫彩瑛說道。
「妳又不是不知道上海現在的治安,」名井南端詳著架上一只鑲鑽發條手錶,「妳像個小夥子倒好,我穿的的招搖一點,被人說狐媚事小,被哪家大老闆抓去當小老婆怎麼辦?」
「哪個傢伙抓妳去當小老婆,我就讓父親斷了他的財路。」孫彩瑛用帕子墊手,捧著一個黃金懷錶看,「我生平最恨的就是仗勢欺人。」
「難為上海上流圈子裡有妳這樣正直的人,」名井南傾身,從背後輕輕摟住對方,「我知道妳不忍心。」
身後的溫度透過兩層布料,為孫彩瑛的內心在這夏末淺夜注入一絲暖意,伴著暖意而來的,是一股恬淡的茉莉花香氣。
「是生日送妳的吧?」孫彩瑛倚在對方頸窩,讓花香充盈在口鼻之間。
「嗯,我很喜歡。」名井南在她頭頂輕輕一啄,「起來吧,別人看著呢。」
「看著有什麼?談戀愛違法了?」孫彩瑛裝著氣鼓鼓的說。
「沒什麼,」名井南捏了一下對方的臉頰,「怕人家找妳父親咬耳朵罷了。」
「咬個屁,」孫彩瑛翻翻眼珠,「我兩個哥哥,一個一年在國內沒幾天,一個北京上海兩頭跑,到時候父親要分幾間商行出來減輕負擔,還能指望誰啊?」
「也怪不得老闆把妳當男孩子養了。」名井南笑道。
談笑間,貨架一角的一個懷錶吸引孫彩瑛的注意。
銀色錶蓋上鏤空的雕花雕工細緻,藍色漸層琉璃錶面,附上白金材質的長短針和燙銀數字。
不若那些商界巨擘戴的大金錶張揚,反而能彰顯個人內斂的性格與氣質。
她想到在報社窗邊敲著打字機的名井南。
淨白的面龐不施妝點,細碎的髮絲垂在額邊,有風拂過便會輕輕飄動,她又生得一副好骨相,即便一張側臉擱那兒,也得顯那傲人的五官與淨冽如山泉的清秀。
「阿南,這錶適合妳。」孫彩瑛看著懷錶說道。
「怎麼適合?又怎麼證明妳不是拿名貴的東西討我歡心?」名井南邪邪一笑,淡漠的眸子閃過一絲狡黠。
「人如其錶。」孫彩瑛回了句,轉頭便喊,「老闆,這錶怎麼賣啊?」
老闆聽了叫喚,忙放下手邊工作過來,拿起懷錶看了看,問道,「小姐是送禮還是自用啊?」
孫彩瑛看著在一旁乾瞪眼的名井南當然不能說實話,想都不想便說,「自用。」
「這錶自用很合適的,雖說這銀色材料部份全是白金製,可這雕花、藍寶石錶面,還有內裡零件組裝的功夫都不輸那些金懷錶的,送人稍嫌失禮,這自用啊,抬身價呢。」老闆眉飛色舞地說道。
「那包起來吧。」孫彩瑛說的毫不猶豫,「多少錢?」
「十五銀圓,小姐。」老闆答道。(註1)
「確實不貴。」孫彩瑛付了錢,隨即拉著名井南離開。
逛完街,兩個人找了間餐廳吃飯,末了,孫彩瑛拿出裝著白金懷錶的沉香小木盒,推到對方面前,「諾,妳的七夕禮。」
「這……」名井南面上盡顯猶豫之意,接著一伸手就把盒子推回去,「我不能收。」
「怎麼不能收,我就覺得這錶適合妳。」孫彩瑛舉起手中的高腳杯,映著燭光的酒液透著略帶深色的絳紅,「價格嘛,妳要騙人家說是自己買的也合理。」
「這錶低調歸低調,只是我從妳那裏收了太多東西。」名井南垂著眼,修長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陰影。
「當妳沒送過我東西呢,」孫彩瑛扁扁嘴,「以為掛上我家那幾個老僕人的名號就能呼嚨我嗎?」
「啊,妳知道啦?」名井南臉上表情很是尷尬。
「大小姊問話他們能不老實回答嗎?」孫彩瑛愉快的叉起一塊草莓慕斯放進嘴裡,「妳有的是好腦袋,下次再想點別的把戲來。」
「唉,以為終於有理由拒絕了呢,」名井南一手端著新沏的特等龍井,一手收了沉香盒子,接著迅雷不及掩耳地給對方腦袋上一個暴栗,「孫彩瑛妳個小機靈鬼。」
小傢伙無辜的掩著腦門,「誰讓我是孫家女兒,聰明與生俱來呢。」
「哈,還得配上四個字,『伶牙俐齒』。」名井南笑道。
「不伶牙俐齒以後該怎麼繼承家業啊?」孫彩瑛嘻嘻一笑,「等我哥他們都繼承家業了,我立馬入贅當湊崎家的好媳婦。」
「妳倒是說話算話啊,」名井南叉起手,「別到時候又讓我備嫁妝彩禮,嫁進孫府大院天天讓妳逞口舌之快。」
「行。」孫彩瑛應得爽快,「那這懷錶就是定情信物了,要這樣,妳也得變個信物給我。」
「這有什麼難,」名井南嫣然一笑,掏出一個絨布長盒,「妳打開看看。」
孫彩瑛很是驚喜,掀開盒子,裡頭是一條打好的黑絲綢雜金絲領帶。
「聽妳說不喜歡用令尊不用的領帶,剛好報社有朋友家裡做紡織的,就給妳訂了一條。」名井南支著臉看她,「可還喜歡?」
「喜歡,阿南送的東西都喜歡。」孫彩瑛立刻拆下原來繫著的領帶,換上新的,那領帶本就是量身訂做,繫起來不僅脖子舒服,也不像她爹的領帶過長還得紮進褲頭裡。
比起自己總送貴重的禮物,名井南送禮總是能送在心坎上,雖然老是打著孫家人的旗號這種無用至極的掩護,可從這些小細節上來說,名井南比起某些跋扈的歸國學子,不僅足夠內斂,在處事上也自帶一股文人獨屬的風雅。
這是孫彩瑛在世代經商的家裡感受不到的。
名井南說過父兄早亡,母親棄她不顧,多數的親情都是湊崎家所織就,就連她自己,都已經淡忘親生父母究竟是怎樣的人,只依稀記得,湊崎母提過一次,「妳有阿幸的臉,和妳父親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性子。」
「想必令尊也是個翩翩君子。」說這話時,天色已晚,孫彩瑛打了自家車,送名井南到湊崎家門口。
「不知道,父親只活在別人嘴裡,我也不敢斷言。」名井南回道。
「既然伯母都這麼說了,那一定是的。」孫彩瑛伸手便是一個深深的擁抱,好一會兒才放手,「快進去吧,伯母一定等急了。」
名井南點點頭,推門進去,忽又探頭道,「妳回去也小心點啊。」
「會的。」孫彩瑛揮揮手,看著厚重的橡木門關實了,才上車離去。
***
時節轉眼入深秋,路上行人的袖子漸漸長了、衣服厚了,有些怕冷的早出晚歸也披上外套了。
孫彩瑛近來忙得像是多頭燒的蠟燭,要結的帳一本接一本,有時從天剛矇矇亮一頭栽到深夜,只要有空,便想念起報社窗邊的名井南來。
好歹是把結清的帳交到父親手中,孫承煥接過來只翻了幾下,便擱在一邊,開口,「阿彩,爸有要緊事與妳說。」
「啥事?」孫彩瑛問。
「妳大哥前兩個月在上海談成了一筆大生意,對方條件非常好,合作下來發現他們的專長正是孫氏所缺的,所以……」孫承煥頓了頓,續道,「他們老闆家有個兒子,今年剛滿二十、未嫁娶,性子也算溫順乖巧,不如……」
「爸,我有喜歡的人了。」孫彩瑛截斷父親的話頭。
「喔?」孫承煥眼睛一亮,「是哪家的公子啊,要是門當戶對,爸立刻作主讓妳們成婚。」
「不是公子,是小姐。」孫彩瑛答得直白,「九街的湊崎家養女名井南。」
「女的?」孫承煥臉立刻黑了,「女的也罷,可湊崎家的輝煌早就過了,現在的湊崎氏只剩一對母女,她家嫡出的女兒還是個舞女。」
「那又怎麼了,她乾姊一晚的酒錢能抵妳女兒舖子裡半月的帳。」孫彩瑛一屁股往沙發上一坐,「她本人的一篇稿費也就這樣多,這算門當戶對吧?」
「妳怎能如此不顧孫家聲譽?」孫承煥臉色黑如鍋底,「妳要是真跟那女的好了,我孫承煥臉面往哪兒擺,人家問起妳兩個哥哥,我都有話說,妳呢?跟一個女記者好上了是嗎?」
「什麼記者,人家可厲害了,留日學歷,精通三國語言,還寫的一手好文章,」孫彩瑛說道,「家裡都出商人,招一個文人進來有什麼不好,打不定能幫孫家做做推廣呢。」
「一派胡言!」孫承煥語中已有怒意,「妳大哥花了多少心力才談成和管家這個盟友,妳可知道妳的任性會為孫家帶來多大的損失?」
孫彩瑛稍稍抬了些音量,「我又不認識管家兒子,憑什麼和他訂終身?」
「憑妳是我孫承煥的女兒,憑我教妳的經商之道去幫助管家!」孫承煥倏然起身,「妳不喜歡那孩子也行,找一個我孫家能合作的親家,爸也許妳成親,一切婚禮程序嫁妝彩禮爸都幫妳打算,就是跟那女孩子沒得商量!」
「沒得商量也罷,」孫彩瑛緩緩起身,「反正女兒就是個賠錢貨,我親生父親拿來跟商業夥伴結親家的工具。」
她走到父親面前,抬眼直視,「反正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家裡給的錢我不要、房子也不要,那個鋪子看給大哥還是二哥,我淨身出戶,可行?」
「妳敢?」孫承煥一個眼刀橫空飛來,轉頭便喊,「孫興!」
孫家管事孫興立刻在門邊現身,「老爺,有何吩咐?」
「從現在起,給我盯好小姐,除了家裡和舖子,任何額外的行程沒經過我同意都不許去。」孫承煥說道。
「爸!」孫彩瑛對此處置自然十分不滿,「這是禁足,您憑什麼!」
「這事兒簡單,妳什麼時候離開那女人,爸什麼時候還妳自由。」孫承煥冷笑道,「算妳執掌舖子以來都沒犯事,我這麼做,已是十分寬厚了,至於這面子妳給不給,四個字,『由不得妳』!」
說完便讓孫興把人帶了出去。
***
對於在孫家發生的事,名井南一無所知,作家的生活很是自在,有稿子的時候按時寫稿交稿,沒稿子有時在家看書,或是去附近幾個省縣的風景名勝走走。
這時節金山區的楓葉開的正好,她很想帶孫彩瑛一起去,可不知為何,那小子最近都不到報社樓下來等人。
既然她不來,她知道孫家那間小舖子的地址,這次,換她去找孫彩瑛了。
***
禁足安安穩穩的過了幾週,孫彩瑛很慶幸名井南從未找來,對於孫興神出鬼沒的監視,她寧可任兩人曾經美好的回憶隨秋風捲殘雲。
自小到大,他從未看過父親震怒至此。
也許是她根本沒認清孫家,自以為那張初出茅廬的伶牙利嘴就能說服在商場征戰多年的父親。
她錯的厲害,即便她小時候曾經打破幾尊名貴的古董人像,都不曾受到如此嚴懲,她很愧疚,對孫家是,對名井南更是。
掛在店門口的風鈴突然發出清亮的聲響,有客人上門。
孫彩瑛抬頭,人如泥塑木雕般呆住。
是她,一頭黑髮被風拂得有些亂,精緻的面容依然恬淡而沉靜,內裡一件純棉女式襯衫,荷葉領口用黑色細緞帶繫了個蝴蝶結,下身一件燙的筆直的西裝褲,搭配黑色黃銅扣皮帶、黑色短靴,外披一件卡其色羊毛長西裝外套。
鮮豔的顏色能襯得她風姿綽約,可這樣素淨的顏色,方能顯她天生不沾人間煙火的氣質。
她來了。
她來了。
孫彩瑛心裡這三個字像防空警報那樣響了又響。
人生一悲,摯愛之人相見只能做素昧平生。
「歡迎光臨。」孫彩瑛開口,隨即低頭,不敢直視那雙宛如秋風瑟瑟的雙眸。
「妳好,我想買幾支鋼筆,國外進口的最好。」名井南唇微啟,竟是真把對方視如陌路。
「有預算麼?」孫彩瑛俯下身去,裝著找東西,實則無顏以對。
「今天只帶了五銀圓的票,請小姐幫我物色點好的吧。」名井南邊說,邊端詳著店裡的環境,驀然,目光停在孫興藏身的牆角處。
孫彩瑛沒注意到這節,只是捧出幾個盒子,開始介紹,「這是德國來的上等貨,出水均勻,握在手上也舒服;這也是德國的,筆頭是工廠的匠人親手雕製而成……」
名井南煞有介事地聽她說完,隨意揀兩只,順道添了些墨水,才決定結帳。
「三圓五角。」孫彩瑛報了價,等著對方付錢。
名井南掏了好一會兒,才理好票子交給她。
孫彩瑛清點過數量無誤、找好錢,把商品細細包好,附上店裡的名片,說聲,「謝謝光臨。」
名井南接過東西,轉身朝店門口走幾步,佇足,開口,「秋深了,別著涼了。」
說完便推了門出去。
過了大半晌,孫彩瑛才意識到那七字是對自己說的,抑在心底的沮喪又如烹煮中的白水般蒸騰起來。
她拉開抽屜,偽作清點銀票,實是想追回銀票上獨屬於那人的觸感,翻過一角,一張便籤乍然出現在堆疊的銀票之間。
牆角後出現腳步聲,推開廁所門,又闔上,估計孫興暫時沒在盯著自己,她迅速將便籤收入衣帶中。
***
直至孫宅的最後一道燭光熄滅,孫彩瑛才敢藉著路燈的微光查看便籤的內容。
「余聞金山楓葉乃上海市一絕,忌汝要務纏身,未能當面一約,若閣下有意,有勞回信至上海報社213室。望平安周知。南。」
寥寥數語,可見自己久未露面,對方是放在心上的。
不僅如此,名井南行事之謹慎也大出意料之外,即使是孫興這樣天衣無縫的監視也讓她硬是鑽了空子。
兩週,於熱戀中的情人就像北極海終年極凍的海水,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讓燎原野火銷聲匿跡。
她多想和名井南一起去看那滿庭緋紅,猶記得去年今時,遍布枝椏的絕色映在她的臉上,即便脂粉未施,也是別具風華。
可如今家庭這堵高牆橫亙在兩人之間,任孫彩瑛如何拍打叫喊,名井南能聽到的,終究是小小便籤上稀薄的文字而已。
「我好想妳,南。」在這境況下,一紙便條有如久旱後的甘霖,再次滋潤孫彩瑛已成桑田的心海。
深秋夜晚的月色美極,可那過度明亮的月光,奪走了多少人甜美的夢鄉。
***
「前日管氏提親,為求避嫌,不能如金山之約,聽聞今朝楓葉生得甚好,若君盼之,勿錯此良辰美景。請恕余不能同往之,今後亦望汝勿念吾,孫某惶恐愧疚,再拜、再拜。」
孫彩瑛念著名井南好,名井南又何嘗不是朝思暮想?
她看完便籤,揉了揉丟進一邊的字紙簍,嘆了口氣。
她早該想到的,孫氏家財萬貫,又橫行商場無數年,身為嫡女的孫彩瑛怎麼能逃脫為家族聯姻的命運?孫承煥又怎麼會看上只是個報社小小作家的自己?
可她的小老虎,有大戶出身的大器,有飽讀詩書的博學,更有與尋常女子不同的不拘與灑脫。
越是想,越是不捨;越是不捨,就越是難以割捨。
思及此處,手中的黃湯杯杯下肚,都無法澆熄那張揚蔓延的相思之苦。
她是初嘗情愛的滋味,原以為是發膩的甜,卻兼有如鯁在喉的苦澀。
「阿南,還沒睡嗎?」湊崎紗夏深夜返家,發現妹妹房間的燈還亮著,便推開房門來看。
名井南靠坐在床角,旁邊散放著幾個已經喝空的玻璃瓶,餘下立著的一瓶也所剩無幾。
「怎麼喝這麼多!」看著平時矜持自律的妹妹喝得爛醉,湊崎紗夏上前握住名井南垂著的那隻手臂,問道。
「都說酒能澆愁,怎麼我喝了,那愁只越發濃厚呢?」名井南一雙眸子早已哭得紅腫,一抬起頭來,蓄著的淚滴又順著臉頰簌簌滑下,「姊姊知道管家嗎?」她說著,從床上摸出一份報紙擲在地下。
湊崎紗夏拾起一看,是一份前兩天的報紙,頭版是孫管兩家大企業即將合作的消息,聳動的標題寫著:「上海商界風波再起」。
「阿彩說管家來提親了,她拒絕不受,便被父親禁足。」名井南將杯中液體一飲而盡,斟完最後的一點酒,「她畢竟是孫家的女兒,養大了就是要為孫家所用。」
「南,」湊崎紗夏喚了一聲,輕輕靠在妹妹身邊,「那妳要怎麼辦?」
「我若繼續纏著她,孫家出面也罷,怕是管家也來為難,那就不只是我倆的事了。」名井南舉盞一笑,笑得極淒涼,涼過秋日天階夜色,「勸君更進一杯酒,出身富商無戀人。」
「那孫彩瑛和妳分了嗎?」湊崎紗夏捏起袖子沾去對方臉上的淚珠。
名井南搖搖頭,「沒分,卻也同分了無異。」
「妳們倆此前如何恩愛,姊姊知道。」湊崎紗夏望著闃黑的天花板,「我相信這事,孫小姐也是萬般不願。」
最後一滴紅酒入喉,名井南放下酒杯,胡亂摸索著地上是否還有不空的瓶子,卻只是徒勞。
湊崎紗夏任著她,自顧自說道,「縱然萬般不願,可這時候,更要去想妳們之間究竟是真心相愛,還是僅止於年少情分。」
「止步於此,是青春年少;長此以往,便是真心實意。誰不想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名井南頰上浮著爛醉的紅暈,神智卻是無比清醒。
「那就別做會讓自己後悔的事情。」湊崎紗夏輕撫妹妹柔順的長髮,「年少輕狂也好,終成眷屬也罷,就要順著心意去,不留遺憾才好。」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另一回事。」名井南眸子裡的顏色如夜幕灰暗,「姊,我好累。」
「那就睡吧。」湊崎紗夏幫著她收起滿地玻璃瓶,「明早我給報社請假,妳多休息點兒。」
「嗯。」名井南應了聲。
湊崎紗夏拎著一堆酒瓶叮叮噹噹的走了,名井南沒立刻躺到床上,只是看著桌上的一角。孫彩瑛送給她的懷錶,正在月光下熠熠生輝。
***
九月二十五,那年秋的尾聲,名井南獨自一人去了金山。
絳紅的楓葉幾乎落盡,只剩滿地鮮紅,遊人也如園中殘留在枝上的枯葉一般稀稀落落。
名井南自嘲這般正好,省得滿園的人讓她看著觸景傷情,掃了出遊的興致。
過去一個月間,她和孫彩瑛聯繫甚少,中秋還問著家裡的月餅好不好吃,過了十天半月便只有噓寒問暖了。
自那日酗酒之後,她只覺得人生再無色彩,只有看到這刺目的鮮紅,才能警醒自己,雖是心死,可這血肉之軀還在這滾滾紅塵中載浮載沉。
「孫小姐,這園中楓葉都快掉光了,怎麼還帶我來呢?」一個陌生的男聲從園子的另一角傳來,讓名井南豎起耳朵,同時閃身藏到一處山石後頭。
「先前只要逢了秋日,我必會同一個相好來賞楓,今年忙舖子裡的事不得空,只能等過季再來了。」那是孫彩瑛的聲音,清清楚楚,「因為和那人有些生分,我想來這裡念念舊情。」
「孫小姐心上有人了?」那男人問道,「那管某豈不是奪人所愛?」
「奪人所愛又如何?」孫彩瑛語中滿是悵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是我身為孫家女兒逃不了的命。」說著,話鋒轉為憐惜,「那人待我,甚是交心,若是得見這滿園楓紅落盡,定是傷情得很了。」
「聽妳說來是個專情種。」男人說道,「妳因我負了他,我只能盼他個婚姻圓滿了。」
「但願如此。」孫彩瑛嘆了口氣,「且不說這個,令尊說婚期定在什麼時候?」
「父親說要年後了,實在忙不過來。」男人答道,「也讓孫家有時間準備準備。」
男人話音才落,名井南便從山石後現身,正當著兩人的面,那面色是悲恨交織。
管家公子只知道山石後出來個美人,孫彩瑛卻是頭上響了聲焦雷一般。
「妳要嫁了,是嗎?」名井南一字一句說著,彷若開口都費了極大力氣一般。
孫彩瑛看了看光禿禿的枝頭,好一會兒,才說,「是,我本要親自去湊崎家找妳說,令堂說妳在這裡。」
「你們什麼時候……」名井南正待問,可那心中苦意泛上喉頭,愣是讓接下來的千言萬語梗在一處,就是無法說出口。
「管先生,請你迴避吧,我和她說幾句話。」孫彩瑛轉頭說了聲。
「請便,妳若說好了,我就在園子門口。」管家公子說罷,轉身便去了。
管家公子去後,兩人相對無言良久,還是孫彩瑛先開口,「阿南,是我對不住妳。」
「這便是妳和我生分的理由嗎?」名井南指著園子門口的方向,「看看人家管公子,家裡有錢,人生得又端正,我算什麼呢?」
「阿南,是我父親……」孫彩瑛正要辯駁,被生生打斷,「那是妳連婚期都瞞著我的理由嗎?」名井南說著,看著面前這張曾經令自己魂牽夢縈的臉龐,不僅生不出恨,只有如潮水般的失望劈頭蓋臉而來。「阿彩,我以為我們之間是無話不談的。」
「我說了,此事是我對妳不住。」孫彩瑛臉色黑了一層,眉頭也逐漸緊鎖。「妳要恨便恨,這惡果,我只能自己吞下。」
「哈,」名井南冷笑一聲,「妳說的輕巧,往年深情猶在跟前,妳叫我從何恨起?」
「對不起。」事到如今,孫彩瑛感覺自己再說什麼也是枉然。
「妳也不用說對不起,以前的事,就當我天真懵懂無理取鬧吧。」名井南說罷,轉身要走,身後人一個箭步上來,將她從背後摟了個嚴嚴實實。
名井南愣住,本已如鐵石般的心腸軟下來,不忍撥開腰間的那雙手。
孫彩瑛這才知道,她瘦了,雙手無須施力就能咯到肋骨尖兒,再厚的胭脂水粉都掩不住凹陷的雙頰。
「阿南,別走,再讓我抱抱妳。」俊秀又略帶英氣的臉龐埋在對方單薄的後背上,孫彩瑛的聲音悶悶的,像是被關在甕裡說話一般,「妳這一去,我們就真的是恩斷義絕了。」
「我於妳無恩,妳對我無義,焉有恩斷義絕之說?」名井南的聲音顫著,宛若枝頭不願被強風吹落的枯葉,「妳我終究只是緣淺,別太瞧得起自己。我只問一句,妳於我,是真情還是假意?」
「我若是假意,自不會和父親說與妳相好之實。」相比對方寒心到極致,她卻是無來由的冷靜,「如今我和未來的夫君來遊園也被妳撞見,我說得再多,妳的真心,終究是被我作踐了。」
名井南輕輕挪開環在腰間的那雙手,回身,白皙修長的五指輕顫,緩緩撫上對方的臉頰、下顎骨,接著是後腦杓,將這張臉向自己緩緩拉近。
孫彩瑛欠她一個耳光,可因為無恨而無從下手。
兩人的距離越來越近,在唇瓣相觸的前一刻,名井南微一偏頭,兩人的一吻都落到了對方頰上。
「唇瓣上的這一吻,且留給管公子吧。」名井南退開一步,再退開一步,踉蹌的身影在孫彩瑛的婆娑淚眼中模糊,最後,若冬初最倔強的那股秋意一般,裊裊散去。
***
那年冬,對名井南來說孤冷異常,嬌弱的身子架不住洶湧而來的朔風,大病一場。
在高燒的夢魘中,總會出現一個矮小可愛的身影,在孫家舖子那街的街角,笑開一雙虎牙與梨渦,揮著手叫喊,「阿南,我們去看楓葉。」
她總是萬分歡喜地跟上去,可末了,那人會走進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世界,任她如何尋找都是徒勞,而夢醒時,不是寂靜漆黑的漫漫長夜,就是孤獨沉默的白日懨懨。
她知道湊崎母和湊崎紗夏總是在病榻旁默默護著,連姊姊相好的金醫生也來過多次,好歹撐過元宵,吃了一碗湊崎母親手熬的紅豆湯圓,她的精神才慢慢恢復。
一月二十早上,病中無事,她望見靜靜擱在桌上的白金懷錶。
她凝視著它,也許幾分鐘,也許幾小時,突然,她有了力氣,下床把那懷錶緊緊捏在手裡,翻出壓在衣櫃底最濃的那瓶威士忌,拔開瓶塞,仰頭一飲而盡。
酒瓶摔碎的聲音引來了湊崎紗夏,她驚慌失措地推開房門,說了很多話,可名井南一句都沒聽進去,塵世中的那些聲響於她只是無關緊要的喧囂,直到她看到自己鮮血淋漓的雙手,而那鮮紅的中心,白金懷錶靜靜躺在血泊中,指針依然若無其事地走著。
長達數個月的啞然後,她看著姊姊,開口,聲音低沉嘶啞,「姊姊,我疼。」
那疼,是皮肉傷的疼,更是心傷難癒、畢生難忘的疼。
她看到帶血的懷錶,才幡然醒悟,若是自己離開這世界,便叛了湊崎家的親情;苟且偷生,才能在那人心底留下念想。
她哭了,安靜地哭了,渾身顫慄如入十里冰窖,氾濫成災的淚水浸濕墊在下頭的棉質衣領。
***
冬去春來,種在大宅陽台上的梔子花含苞待放,名井南也可以在宅子裡走動了。
因著湊崎母有事去了外地,湊崎紗夏請了假留下陪妹妹。
這幾個月名井南的變化甚是令她刻骨銘心,從去年九月二十五回家的失魂落魄,病了整個冬天,一個好好的人瘦的幾乎只剩骨架子,一月二十五,她似是想通了什麼事,在房裡灌著酒,又用酒瓶的碎片割破自己的手掌,春天來時名井南身量恢復不少,可穿著合身的襯衫仍是有些鬆垮,此刻正坐在桌子前用打字機寫東西。
「歇會兒嗎?」湊崎紗夏熱了一碗紅棗桂圓湯,放在桌邊的窗台上。
名井南在鍵盤上飛舞的手指頓了頓,她的目光凝在窗外,似是連個簡單的問題都得讓她思之再三。
「也好。」過了一會兒,她開口,「姊姊,一會兒能陪我去一趟報社嗎?我去交稿。」
「當然好。」湊崎紗夏眉間一鬆,「妳臉白,讓姊姊幫妳上點妝可好?」
名井南沒有拒絕,只是愣愣地看著鏡子。
她的顴骨天生便不明顯,此時還是能看出一些陰影,過往淡漠的眼神成了無神,一雙紅脣蒼白得像是冬日不帶雜色的純雪,向來整齊的黑髮看著蓬鬆而凌亂。
「怕什麼,妳可是美人胚子。」湊崎紗夏似是看出了她的擔心,幫著梳好頭髮,拍點腮紅在頰上,再用口紅掩住她那最折精神的白唇。
名井南看著自己像了回人,稍稍寬了心,下身換上一件西裝褲,依然是披著卡其色羊毛長外套,頸間戴上一條粉藍色圍巾,沖淡她身上過於冷冽的氣息,看著更親人一些。
***
春初街上還是有些涼,名井南久未接觸外頭的寒氣,走出門時還是不禁縮了縮頭。
「冷嗎?」湊崎紗夏看著身邊幾乎縮到沒脖子的人,有些擔憂地問道。
「無事,足不出戶,不習慣。」名井南緊了緊手上抱著的稿子。
「妳要是冷就說,姐姐這條圍巾給你。」湊崎紗夏指了指脖子上圍的紅色毛線圍巾。
名井南點點頭,不語。
兩人走到一處街角,忽有鑼鼓喧天自報社方向來,湊崎紗夏好奇地探了探腦袋,看清之後,拉著妹妹的手,便要轉身繞道離開。
名井南被拉得莫名其妙,走了幾尺遠,喊了好幾聲「姊」才讓湊崎紗夏停下來。
「是她的成親隊伍,姊姊會忍心讓妳看嗎?」湊崎紗夏停步回身,說話間還帶著些許快步之後留下的喘息。
「姊,我放下了。」日光映照在名井南瀲著水光的眸裡,卻更顯她的誠心懇求,「我那日不曾與她訣別,今日,便權當是道別吧。」
湊崎紗夏拗不過,只好擺擺手說道,「唉妳去吧,我就在這裡等著。」
名井南重新回到轉角,這一耽擱,娶親的車隊已經由遠而近,正中央那台綁著大紅花的黑頭車,肯定就是新娘和新郎倌的坐駕了。
禮車緩緩接近,名井南垂首琢磨自己藏身人群,孫彩瑛說不定根本沒機會看她一眼。
再抬頭時,正好禮車通過,便和車裡偷偷掀開蓋頭的孫彩瑛來了個四目相對。
這重逢,無聲、亦無顏色。
孫彩瑛眼中的她,僅僅別離數月,身上的清冷更甚,甚至有些淡漠,只頸間那方淺藍圍巾稍稍中和一些寒意,面上雖有脂粉,卻怎麼也無法掩飾那大病初癒的蒼白臉色。
名井南眼中的她,許是多在家族間周旋之故,小老虎身上的那股衝動勁被磨去,沉穩冷靜的外表下,卻藏著對意中人藕斷絲連的感情。
只見孫彩瑛面上的表情由好奇漸漸轉為驚訝,接著嘴唇煽動,似是喊著什麼話,企圖讓名井南知道些什麼,可那人終究只是將半張臉隱入淺藍圍巾之後,垂眸,一個極為含蓄的頷首,一轉身,便如渺渺一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還好嗎?」看著妹妹從人群裡鑽回來,湊崎紗夏一把揪住,取下大紅圍巾就往她脖子上套。
「我很好。」名井南笑著,清冷的面龐添上一絲暖意,「她還念著我,可惜這往後的路,只有漸行漸遠了。」
「也難為妳想得開,」湊崎紗夏撫了撫胸口,「尋死覓活的,妳難受,我們也難受。」
名井南頓了頓,轉頭看姊姊,說道,「便是想到姊姊和母親,才活得下來。」
湊崎紗夏被這話噎住,半晌不知道拿什麼接,只輕撫妹妹的背脊以示安慰。
「我要是這樣去了,黃泉之下見到父親,他會罵我的。」名井南抬頭,看著遠處熙來攘往的行人。
「叔叔才不會這樣呢,他就妳一個女兒,不疼妳疼誰。」湊崎紗夏隨手折了路邊的牡丹插在鬢邊,說道。
名井南看了她一眼,聳聳肩,聞著街邊稀稀疏疏的梅花香,自顧自詠起詞來,「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對江天、分付他誰?空自憶,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知。」(註2)
湊崎紗夏沒讀過書,自是不明所以。
「姊姊不必追究,我不過是抒發一些念想。」名井南回頭看著呆若木雞的姊姊,說道,「前面就是報社了,姊姊在此稍候,我去去就來。」
又是一陣微風吹來,吹得報社一沓沓厚厚的白紙唱了齣「快樂頌」,卻吹不出心死之人心湖上的一點漣漪。
從前她輕信了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如今,只怕是情深意篤、金玉良緣,也敲不開這扇緊閉的心門了。
註1:以民國二十年的物價水準算,有言「一般人工作十天賺不到一銀圓」,所以以現每月基本薪資2萬4000台幣計算,一銀圓折合新台幣8000元。
註2:出自李邴《漢宮春‧梅》,此詞風格疏淡雋永。詞中梅的形象给人以清高拔俗的感覺。為了塑造這樣一個形象,作者選擇了「瀟灑」、「稀」、「清淺」、「冷落」、「微」、「淡」等一系列色淡神寒的字詞,刻畫梅與周圍環境,儼如一幅水墨畫,其勾勒梅花骨骼精神尤高。
***小狂碎碎念***
繼甄嬛傳之後我開始去翻裡面演員演的其他作品看,其中《情深緣淺》算是裡面讓我印象滿深刻的。
這印象深刻是「怎麼這種卡司可以被噴成這樣」,然後我看了就懂了,選角問題真的很大,怪不得人家要噴。
兩位女主角分別是38歲的蔣欣和50歲的劉嘉玲,這根原著設定的年齡差可不小啊,然後劉嘉玲雖然普通話講得不錯可是那個粵語口音真的是讓我分分鐘出戲。
對比前一版本林心如+蔣勤勤的雙女主組合那活該被噴、被公開處刑了。
悄咪咪說一句蔣欣劇後期的演技真的很好![]()
至於半生緣原著很多設定是跟我三觀不符的,我就拿掉了,詳細的就後記裡再見吧~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png)

